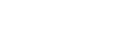距离年三十还有好几天,母亲的几通电话总会把话题绕到什么时候回家上面,在电话里,听着母亲细数着准备的年货和提前做的年夜饭“硬件”(酥鸡、丸子、红烧肉),总会感受到越来越浓郁的年味和越来越近的年关。儿时,最喜欢过年,因为过年不光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花,还能吃到父母亲手做的年夜饭,没有多么丰盛,但却香甜可口,每年年三十吃团圆饭是我们家打我记事起的传统。已亥春节,由于工作原因,我成了家里团圆饭的缺席人员。
正月初一,带着思乡情节和记忆中的年味,我携妻带女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故乡榆林市子洲县马蹄沟镇吴家沟村,一个算不上贫瘠,却因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徒生荒凉的地方,虽然因春节增添了许多烟火气息,但还是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独自过年的现象。小村距我上班的地方锦界有200多公里的路程,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的回家的路上,四岁的女儿一个劲问我:爸爸何时到家。妻子一直帮我解答,快了……。
临近家门,远远的望见了站在硷畔上守望的母亲,依旧是熟悉的家门,依旧是亲切问候。到家两个哥哥帮忙提东西,三个侄子侄女翘首以盼三爸给他们带回来的好吃的,拉着四岁的女儿去一边分享食物。刚进家门坐上桌子,父亲便端上了热腾腾的饺子,两个嫂子帮忙拿碟端碗,香气弥漫的饺子和家人的热情消融了我缺席年夜饭的愧疚心里。
和父母亲的攀谈中,知道了去年家乡的变化:乘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村里先辈们用脚走出来的土路,成为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的荒草被太阳能路灯覆盖,改变了村里天黑摸路走的习惯;随着宽带网络进家门,人们天黑看电视睡觉的习惯也有了延缓,开始关注新闻和国家大事的人员渐渐多了起来;先进的娱乐设施和村广场文化也替代了小赌怡情的情调;大量的三农政策挽留住了不少进城务工的青年,缓解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总之,惬意的生活正在渐渐向着全面小康迈进。
吃过饺子,不见了母亲,却听见厨房传来了叮当声,还有熟悉的似曾相识香味弥漫,深吸一口气,依旧是年的滋味。傍晚,父亲燃放了年三十存留的花炮,看着母亲亲手做的酥鸡丸子、红烧肉,父亲摔的拿手碟子,依旧有童年的菜色,也有新奇的特色,但每一口饭菜里,都包含的是父母最真诚的爱。父亲拿出了珍藏的美酒,喝团圆酒的时候,上小学的侄女说:今年的年过的真好,吃了两顿年夜饭。童稚的话语却令我感受到了更深的暖意。
高中毕业便离开了小镇村庄,而过年便成为我以及许许多多像我一样在外漂泊年轻人情系故土的纽带。每次回家感受小镇村庄的年味,似乎也成为了弥补父母家人爱的方式。年味里有家人、有团圆、有童年的记忆,有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变迁,生活在变好,记忆中牵连故土的年味乡愁依旧没有改变。
返程时,带着父母准备的村里最上等的年货酥鸡丸子红烧肉和提前在镇子上买的果馅、千层饼,看着依旧在硷畔随着每次守望与送行而渐渐老去父母,心中有种莫名的沉重,手中领着的东西也变得有了分量,像是带走了父母的牵挂和整个小村的年味。(钟阳)